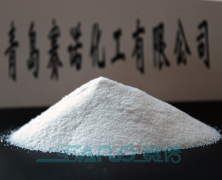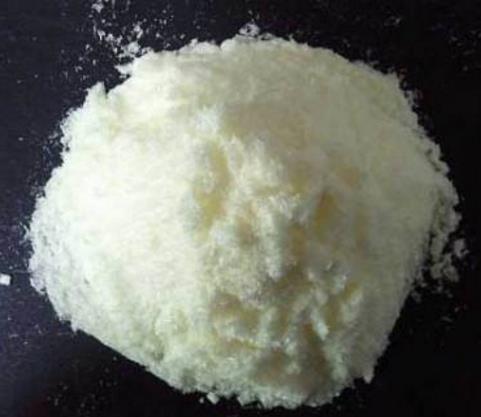3D 打印會顛覆傳統制造嗎?,聚乙烯蠟生產廠家為您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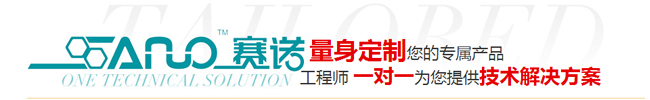
3D 打印會顛覆傳統制造嗎?,聚乙烯蠟生產廠家為您分享博士研究生王智的觀點。
幾年前我還在讀本科的時候,知道了3D打印,我還記得那個時候讓我對這個技術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沒有打不出,只有想不到”。
是啊,多么吸引人的技術啊,多么自然而巧妙的想法啊,機械制造專業的我開始對專業課上的一些東西開始不屑,干嘛要學這些馬上就要被淘汰的東西呢?就像CAD取代手工制圖,Pro/Engineer,SolidWorks之類的3D建模軟件又逐步取代二維CAD繪圖一樣,我也幻想著日后機械制造可以告別沙塵漫天、機器轟鳴、鐵水鋼包、機床電鉆……日后的制造將只需要人們在計算機前拖動鼠標繪制三維模型,然后優雅地點擊“打印”,剩下的就是機器的事了。這也難怪,明明已經是Intel i7的時代了,課堂上講的還是8086架構的CPU——那時的我堅信鑄鍛焊機加工熱處理這些看起來低端又原始的東西早晚要被淘汰的。
各種新聞媒體讓人們不斷地看到新技術的能量:3D 打印造出了槍支,造出了飛機模型,造出了飛機部件,甚至造出了房子!聽說以后還可以3D打印人體器官,器官移植再不用擔心供體來源,也許長命百歲也不再是夢!面對著如此美好的未來,人們堅信,沒有打不出,只有想不到。
盡管曾經有過對傳統制造技術的不屑,盡管我的專業課成績并不算高,但幾年的科班訓練還是讓我在面對3D打印的時候保持了一定的冷靜。我意識到,3D打印是很好的技術,但要取代傳統制造,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或許永遠也取代不了。
3D打印有很多優勢,我每次做presentation的時候都要講一遍:它能制造出傳統制造方法難以制造或不能制造的復雜結構,增材制造的方式相比于傳統的減材制造節省了材料,不需要費時又昂貴的模具,以前需要多道工序制造的產品通過3D打印可能一步成形……比如目前的芯片制造工藝包含了曝光(lithography)、刻蝕(etching)、氧化(oxidation)等一系列的工藝環節,而其中的每一個環節又包含了很多小的工藝環節,更麻煩的是,塵埃和微粒是生產芯片過程中的致命敵人,因此整個的生產環節必須在超凈間里完成,而維持一個超凈的環境成本又很高。一枚芯片往往是多層的,這意味著以上的過程需要被重復很多次,因此,制造芯片是一件耗時又費錢的事。還有,相信我,長時間工作在超凈間里絕對不是什么愉快的體驗。如果未來人們可以用3D打印制造芯片,那么制造周期就將會大大縮短,因為我們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工藝環節,成本也可以大大地降低,因為我們將只需要一個很小的超凈環境。順便,制造芯片的過程也會愉快很多。當然,現在我們還是做不到的,那么未來我們實現了3D打印芯片Intel是不是就要倒閉了?也不一定。
3D打印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尺寸精度。還是上面的制造芯片的例子,人們現在已經掌握了14納米的硅工藝,那么3D打印可以做到多少呢?我找得到的最好的3D打印機精度可以到100微米(1微米=1000納米),Wikipedia上說更好的可以達到16微米,但這顯然不夠好,即使不同Intel的工藝比,對比傳統機械加工也完全沒有優勢,很多小型的機械加工廠對一些產品的尺寸精度要求也可以達到半個絲(1個絲=10微米)。我PhD的研究內容是高精度3D打印的控制算法,把材料熔化再堆積成形的3D打印是很難達到10微米以下的精度的,原因是材料在噴頭處形成的液滴直徑大概就有10微米,用直徑10微米的液滴來達到10微米以下的精度幾乎是不可能的。學術界有一些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其中的一種叫做Electrohydrodynamic-jet Printing,簡稱E-jet Printing,它的原理是在噴頭和打印平臺之間施加一個受控的電場,材料中的電荷受到電場的驅動會在噴頭尖端形成錐形(Taylor Cone),Taylor Cone尖端的直徑將遠小于10微米,如果繼續施加電壓,那么尖端的材料將被沉積到平臺上,形成一個小直徑的材料液滴,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實現高精度的3D打印。在我們的實驗室里,可以實現1微米甚至1微米以下的精度,但由于打印過程本身的一些特性,我們并不能保證穩定的精度輸出,這就是我PhD研究要做的工作,通過空間的迭代學習控制算法來試圖提高打印的精度。在我研究的經驗和所見范圍來看,1微米的精度幾乎是目前能達到的最高精度,而從學術界到廣泛的商業應用之間往往還有一個過程。因此,僅就芯片制造這一領域來說,短時間內想通過3D打印技術來挑戰Intel是不太可能的,因為硅工藝也在一刻不停地飛速發展著。但是,并不是所有時候人們都需要14納米工藝的芯片的,如果3D打印芯片可以成功,那么在集成度不太高的應用場合,3D打印技術就可以大大地降低成本、縮短周期。
3D打印要面對的第二個問題,是材料受限。顯然,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能夠3D打印出來,據我所知,目前常見的3D打印機是熔化高分子材料例如加入聚乙烯蠟的ABS塑料后再成形,也有一些3D打印機可以打印特定的金屬材料。當然這里還有一個3D打印的定義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幾個相關的名詞,在不同的場合都曾經被叫作過3D打印,比如快速成形(rapid prototyping),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在我的印象中,并不存在一個廣泛公認的3D打印的定義和范圍,學術界內部交流似乎并不常用這個詞,但科學家們除了做研究還要“推銷”自己的想法(sell ideas),所以在傳播自己的研究時會常常用到3D打印這個名字,而媒體上的3D打印包含的范圍就更廣。在這樣的現狀下,經常出現一些人說3D打印不能做什么,但是另一些人引用媒體的報道來反駁的情形,其實彼此的“3D打印”并不是同一個定義。最夸張的,我曾經在知乎評論里看到有人說等到人類實現原子級別的3D打印的時候,現在的一切問題就都不是問題了吧。唔,至少我個人并不覺得人類實現那種技術的時候,它還會被叫作3D打印。
3D打印要面對和另一個問題,是產品的性能,特別是機械性能,這也是“沒有打不出,只有想不到”這句話最大的問題。普通大眾對制造的理解往往只是用一種特定的材料實現一個特定的外形,這讓3D打印看起來很完美。對材料性能的理解,粗淺點的,覺得鐵和木頭有區別,鐵和鐵之間區別不大,或是鐵合金和鐵合金之間的區別在于鐵和碳的比例,改變材料的性質只是改變合金中不同成分的比例。在機械制造業內的人看來,這當然不對。記得武俠小說里鑄劍要把鐵燒得通紅然后淬火么?記得某手機發布會上的“奧式體”么?記得化學課上學過的金剛石和石磨都是碳單質么?記得足球烯和碳納米管么?材料的微觀結構對材料的性能影響很大,金屬材料中有“金相”的概念,上面提到的“奧氏體”就是一種金相,它表征了晶體的微觀結構。我本科畢業后就不再研究材料了,好多東西都記得不是很清楚了,但依然記得對材料的各種冷熱處理可以很大程度上改變材料的性能,比如各種熱處理,冷作硬化,表面處理等等。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本科金屬工藝實習的時候手工做的小錘子,因為沒有經過熱處理,想要敲釘子但硬度還沒有釘子高,后來就只好用來敲核桃。而現有的3D打印技術,對材料微觀結構的控制極其有限,對材料性能的控制也非常非常有限。新聞中說有人用3D打印打印出了手槍,但那只是實現了簡易的結構和功能,幾乎沒有可靠性和耐用性可言。和上面提到的硅工藝類似,傳統的材料科學和制造工藝也在一刻不停地發展,3D打印想要完全取代它們,很難。
這里再多說一點器官3D打印。我本科畢業設計就在做生物3D打印,當時我的指導老師第一次跟我說要用細胞打印肝臟的時候,我覺得這真是個偉大的想法,感覺自己在做一件酷得不得了的事情。當然,你不能指望一個本科生打印出一整個肝臟來,那打印個人造血管怎么樣?唔,要求好像還是高了點,那么打印一個人工血管壁組織吧,一層內皮細胞、一層平滑肌細胞組成的雙層組織。打印的材料呢,是干細胞,也就是“萬能細胞”,干細胞具有分化成任意細胞的能力。可是把細胞一個一個堆起來它們就會自己長成組織了么?當然不會,所以要把細胞和特定的基質材料混合在一起,在4攝氏度的低溫環境下打印成形,然后把干細胞培養起來,加入特定的生長因子,向內皮細胞和平滑肌細胞轉化。聽起來不難,是吧?可是一個學期下來,中間的艱辛真是數不勝數。細胞并不會按照我們的想法生長,有的時候也不會按我們預想的方向分化,搞不好還會全部死掉。當然,最后我的確在我的組織樣品里找到了小片的內皮組織和平滑肌組織,但我覺得叫它們細胞團可能更合適。好吧,問題還沒完,即使我順利地得到了內皮組織和平滑肌組織,怎樣控制它們按雙層的膜結構生長呢?又怎樣形成血管呢?如果你看過肝臟的血管網,你會對打印肝臟絕望的……打印像肝臟這樣的復雜器官,和打印一個肝臟的模型比起來,只是看起來很美好啊。把不同的材料按三維坐標堆積起來,一個器官的模型就打印好了;可是把不同的細胞按照它們的位置堆積起來,我們并不能得到一個肝臟。3D打印器官目前也有一些進展,比如打印膀胱和心肌組織,當然,和肝臟比,打印這些器官的難度就低得多了。總地來說,3D打印器官并不是完全不可行,但這需要基礎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
3D打印當然是很好的技術,但是技術不是用來迷信的。人類的制造技術發展到今天,沒有哪一種制造技術可以單打獨斗地解決所有問題,相信3D打印也不能。3D打印和傳統制造之間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沒必要非要用一種去取代另一種。3D打印可以是現有制造技術的一個非常好的補充和完善。同時,3D打印更大的意義在于讓更多的普通人可以更方便地設計和制造自己的產品而無需借助于工廠。建筑設計師們可以快速地打印模型來驗證自己的設計,藝術家們可以更自由地創造藝術品,老師們可以更方便地把書本上的東西變成學生們看得見摸得著的模型,孩子們可以DIY自己的玩具……3D打印也許真的可以改變世界,但或許不是以人們之前想象的那種方式。
來源:王智科學網博客
作者王智,系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博士研究生